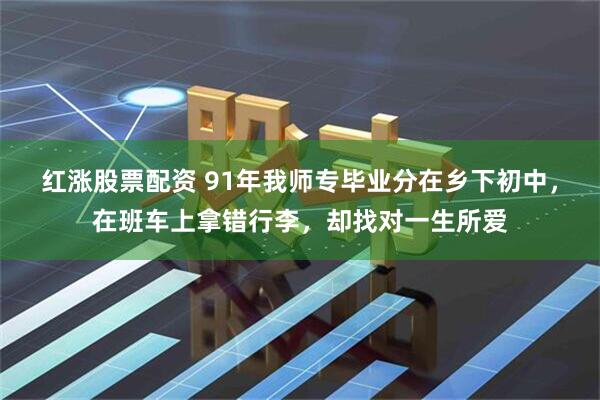
人们都说,命运这东西,信则有,不信则无。搁在1991年的那个夏天以前,我是不信的。我只信我爹说的,人要走正道红涨股票配资,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。
可就因为在班车上拿错了行李,我不仅找回了我的全部家当,还找回了一个媳妇,一个陪了我一辈子的女人。
从那天起,我就信了。有时候,命运给你关上一扇门,就是为了让你走对另一条路,遇见那个对的人。
01
1991年,我从师专毕业。那时候毕业是国家分配,我心里头一直盼着能分回县城,离家近,条件也好。可名单下来那天,我看着墙上那张红纸,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。
“清水乡中学,王建华。”
清水乡,我听都没听过。后来找人一打听,才知道那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乡,从县城坐班车过去,得在土路上颠簸四个多钟头。
展开剩余89%同学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,有的分到县一中,有的留在了城里的小学,就我一个,被发配到了山沟沟里。
出发那天,我爹送我到汽车站,一路上话不多,就是不停地抽烟。临上车,他把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塞我手里:“到了那边,好好教书,别给咱家丢人。”
我点点头,心里五味杂陈。
我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旅行包上了车,那是当时最常见的包,结实耐用。包里装着我全部的家当:两身换洗的衣服,几本专业书,还有我爹给我的那支钢笔。
班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,行李都堆在车厢后面。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,一路看着窗外的景色从楼房变成平房,又从平房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,心情也跟着沉到了谷底。
四个小时后,车在一个尘土飞扬的站牌前停下,售票员喊了一声:“清水乡到了!”
我赶紧起身,从后面行李堆里拽出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,急匆匆地挤下了车。
学校派了人来接我,是学校的教导主任,一个姓李的中年人。他很热情,帮我扛着行李,领我去了学校。
学校比我想的还要破旧,几排红砖平房,操场就是一片黄土地。我的宿舍在最边上,一间小屋,一张木板床,一张掉漆的书桌。
李主任走后,我准备把东西拿出来收拾一下。可我一打开帆布包,整个人当场就愣住了。
包里根本不是我的东西。几件女式的碎花衬衫,两条长裤,几本言情小说,还有一个粉红色的日记本。
我脑子“嗡”的一下,冷汗立马就下来了。我的包呢?我的毕业证、派遣证,还有我爹给我的那支钢笔,可全在我的包里啊!
02
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。这可怎么办?班车早就开走了,那个年代没有电话,想找个人,简直是大海捞针。
我瘫坐在床上红涨股票配资,看着那个不属于我的包发呆。那一刻,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了。
冷静下来后,我想,唯一的线索可能就在这个包里。我怀着一丝愧疚,打开了那个粉红色的日记本。我不识字,但我总得找找看有没有名字或者地址。
翻开第一页,一行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:“林秀英,清水乡卫生院。”
我心里一阵狂喜,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有名字,有地址,那就还有希望!
第二天一大早,天刚蒙蒙亮,我就出了门。跟学校看门的大爷打听了卫生院的位置,一路小跑着就去了。
卫生院就在乡政府旁边,一排小白房,空气里飘着一股来苏水的味道。
我走到门口,心里七上八下的,正犹豫着怎么开口,就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她扎着一条长长的麻花辫,眼睛又大又亮,正低头跟一个小患者说话,神情特别温柔。
我一眼就认出她了,昨天班车上,她就坐我前面不远。
我鼓起勇气走上前,声音都有点抖:“同志,请问……你是林秀英吗?”
她抬起头,有些惊讶地看着我。
我赶紧把手里的帆布包往前递了递:“我……我叫王建华,是昨天刚到乡中学报到的老师。在班车上,我好像……拿错你的包了。”
她一听,先是一愣,随即脸上露出了又惊又喜的表情:“原来是你拿了!谢天谢地,我还以为丢了呢!”
她也急忙从屋里拿出另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,我一看,跟我的那个真是一模一样。
“我的证件都在里面,急死我了。”她说着,脸颊微微泛红,有些不好意思。
我们俩交换了行李,打开检查了一下,东西都没少。我紧紧攥着我爹给我的那支钢笔,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03
就这样,我认识了林秀英。
我们俩的经历很像,都是刚毕业,都被分配到这个陌生的小乡镇,一个是新来的老师,一个是新来的护士。
共同的境遇让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。
那时候乡下的生活很单调,没什么娱乐活动。下了班,我俩就常常在乡里那条唯一的小街上碰见。
有时候,我去卫生院找她,借口是头疼脑热,其实就是想看看她,跟她说几句话。她总是很耐心地给我量体温,开点药,然后嘱咐我多喝水。
有时候,她会来我们学校,说是找李主任有点事,但总会绕到我的宿舍窗前,跟我聊上几句。
我们聊工作,聊理想,聊远方的家人。我发现她不仅长得好看,心地也特别善良。乡里有些老人舍不得花钱看病红涨股票配资,她就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药。
渐渐地,我对她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每次看见她,心跳都会快几分。我知道,我这是喜欢上她了。
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,是在那年冬天捅破的。
冬天的清水乡特别冷,滴水成冰。一天夜里,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突发急性阑尾炎,疼得在床上打滚。
我二话不说,背起那个学生就往卫生院跑。冬天的夜路又黑又滑,我摔了好几跤,赶到卫生院的时候,已经浑身是汗。
那天晚上正好是秀英值班。她一看情况,立刻就忙碌起来,打针、消毒、联系乡里的拖拉机送孩子去县医院。
等把孩子送上车,天都快亮了。
我俩站在卫生院门口,哈出的气都结成了白霜。
“建华,谢谢你。”她看着我,眼睛在晨光里亮晶晶的,“要不是你送来得及时,那孩子就危险了。”
“你才辛苦,忙了一晚上。”我心疼地看着她冻得通红的脸。
她笑了笑,低声说:“你知道吗,我当初选择当护士,就是觉得能救人,是件很了不起的事。就像你当老师,能教书育人,也一样了不起。”
那一刻,看着她温柔的笑容,我再也忍不住了。
“秀英,”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,开口道,“我……我喜欢你。从第一次在卫生院门口见到你,就喜欢你了。”
她愣住了,脸“刷”地一下就红了,红到了耳根。
我紧张地看着她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过了好半天,她才像蚊子哼似的,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就那一声“嗯”,比我听过的任何话都动听。我知道,她答应了。
04
我和秀英的关系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乡里的日子虽然清苦,但因为有了彼此,再苦的日子都觉得甜。
我们一起在河边散步,一起在供销社买东西,日子过得简单又幸福。
第二年秋天,我们就结婚了。
婚礼办得很简单,就在学校的食堂里摆了两桌酒。李主任是我们的证婚人,同事们都来祝贺我们。
没有三金,没有彩礼,她就带着一个装着几件衣服的箱子,嫁给了我。
婚后,我们就住在我那间小小的宿舍里。屋子虽小,但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,窗台上还养了盆绿油油的吊兰。每天我下班回来,总能看到屋里亮着温暖的灯,闻到她做的饭菜香。
那时候,我才真正体会到,什么叫家。
后来,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,一个儿子,一个女儿。秀英一边在卫生院上班,一边照顾家里,我专心教书。我们的工资不高,但省吃俭用,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。
我在清水乡中学一待就是三十年,从一个毛头小子,教到了两鬓斑白。我带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,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,走出了大山,有的留在了乡里,成了建设家乡的栋梁。
秀英也从一个小护士,变成了卫生院的护士长。乡里的人没有不认识她的,谁家有个病痛,都爱找她。
05
一转眼,我们都到了退休的年纪。
孩子们都已经在城里安了家,劝我们搬去城里住,可我们都舍不得这个小乡镇。这里有我们的事业,有我们的朋友,更承载了我们大半辈子的回忆。
我们还是住在学校的老家属院里,房子比以前宽敞了,也装修过了。
天气好的时候,我俩就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
秀英常常会说起当年拿错包的事。
“你说,要是那天我们俩都没拿错包,后来会怎么样?”她笑着问我。
我握住她那双已经有了皱纹但依旧温暖的手,说:“那我就得想别的办法去卫生院找你了,比如天天假装生病。”
她被我逗得哈哈大笑,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前几年,我们一起回了趟我的老家。我爹娘都已经不在了,但那支英雄钢笔,我还一直珍藏着。
我把它拿给孩子们看,跟他们讲我当年刚毕业时的失落,讲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班车,讲那个一模一样的军绿色帆-布包。
儿子笑着说:“爸,你这算是因祸得福啊。”
我点点头:“是啊,那是我这辈子,犯过最幸运的一个错误。”
如今,我和秀英都老了,头发白了,走路也慢了。但每天早上醒来,看到身边躺着的还是那个她,我心里就觉得无比踏实。
我常常在想,如果91年那个夏天,我被分到了县城,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?或许会更安逸,或许会更有钱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我一定会错过那个在清水乡卫生院工作的,扎着麻花辫的善良姑娘。
所以,我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。
人生就像一趟长途班车,你不知道在哪一站会下车,也不知道会拿对还是拿错行李。但只要终点是对的红涨股票配资,只要身边的人是对的,那沿途所有的颠簸和错过,就都成了最美的风景。
发布于:河南省启远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